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 市川博 已有0人评论 2019/3/5 8:54:51 加入收藏
在那次研讨会上,我以横滨市东小学二年级学生的社会科课例“信之旅”为例,做了题为《基础教育课程的国家标准与个性化——以日本小学社会科的课程开发为例》的报告,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教学并不是要将国家制定的教学纲要所规定的教学内容直接灌输给孩子,而是基于规定的教学内容,让孩子们带着“实感”去吸取所教授的内容,以个性化的方式加以理解,在集体中自主地互相学习,开展科学地探究,在获得必要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培育思考力和判断力,形成个性化的思考,从而成为能推动社会发展的人。立足于这样的教育观,我以学生的个体经历、性格和教学实录等为依据,对3个不同类型的学生在学习中发生的思维变化(成长)做了详细分析,并阐述了这一教学实践所具有的意义以及课例研究的方法。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报告能否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赞同,但我希望借这个报告向中国的各位传达日本社会科所追求的课堂教学。报告结束后,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学者跑到我跟前与我握手,她说:“刚才的报告提到孩子们在自主地相互学习的同时,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掌握国家规定的学习内容,令他们在未来可以学以致用,能进行这样的教学实践非常了不起!”
此外,如后文所述,自19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尤其是上海,掀起了愉快教育等各种教育改革。通过这次的研讨会,我得知在中国,对我的报告有着一定理解的研究、实践和体制已经初步成型。在该国际研讨会的全体会议上,钟启泉教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在报告中说道:“大学教师应该进入教育一线,与一线老师们共同进行教材的研究和开发、教学计划的制定和教学实录的分析,在推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的同时,一线老师们不仅能提高教学能力,还能提升理论研究能力。所以,这样的研究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也应该不断推进这样的活动。”我为中国也在朝着和我一样的目标推进教育改革深感庆幸与感动。
通过这次国际研讨会,我与吕型伟先生(原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游铭均先生(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中小学教材办公室主任)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教育管理者、大学和出版界相关人士、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相知相熟,为之后的交流打下了基础,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自1991年8月起,我以华东师范大学为据点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我与大学的教师们不仅讨论了课程和教学问题,还就教师培养和研修等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还给研究生们讲课,因此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的称号。如此一来,我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这种关系在扩展我与大学之间的交流的同时,也为华东师大的教师和研究生来我工作的横滨国立大学进行访学和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外,我还和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教研组及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们就课堂教学的改进展开研讨,给上海市内的教师们做演讲,走访了一师附小、上师大附小等学校,进行观课和评课。我还和钟启泉教授一同访问了昆明和西双版纳的学校。此外,受到上海市教育局的关照,由日语翻译张进先生陪同,我访问了北京、重庆和长沙,与教育界人士广泛交流,观摩教学,参加教研活动。
2. 1994年上海国际研讨会及其后
1994年3月,上海再次召开国际讨论会,主题为“课程教材改革与21世纪人才培养”。那时,我以“日本学科课程结构的改革——以文部省研究开发指定校的实践为中心”为题做了演讲,我介绍道:
自1987年以来,文部省认为作为生存于21世纪的日本人,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及能够自主应对急剧动荡的社会变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相较于“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文部省更致力于推进对“自主学习的兴趣、意愿和态度”的培养、“能施展个性的教育”、问题解决学习,以及终身学习。
为了能够自主应对急剧动荡的社会变化与问题,带着自发的兴趣和热情去自主探究并解决问题的持续学习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文部省将此前评价标准中的“知识和理解”、“思考力”、“判断力”、“兴趣和态度”这四项的顺序进行了大调整: 将“兴趣、意愿和态度”(增加了“意愿”)提到了第一位,将“知识和理解”调到了第四位。为推进学生自主学习,还必须精选教学内容,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以往的学科结构。科技持续地飞速发展,社会也在急剧变化,学科范式的转变也就非常必要。到1970年代中旬,文部省设立了研究开发指定校,以推进课程的自由研发与实践研究,但仍是在既有的学科范围内进行改革。此后,日本的学校获得了可以尝试改变学科框架的许可,于是进行了新设学科或更改学科名称的尝试,一些学校尝试开设了符号科(整合1—2年级语文和数学)、环境科、人类科、表现科、运动游戏科,等等。
在那次国际研讨会后,我与上海教育局局长袁采先生、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主任王生洪先生、市教研室的张福生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钟启泉、沈晓敏、上海师范大学的恽昭世等老师就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给上海市内的教师们进行演讲的同时,还到上海市许多学校观课评课,荣获了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顾问的称号。就这样,我与上海教育界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对上海的教育改革尽了绵薄之力。
四、改革开放后的课程改革
(一)课程改革
中国首先从教育结构开始启动了教育改革。第一步是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等(1977年);第二步是重新研究小初的5·4学制,并过渡到6·3学制(自1980年代在各地开始实施);第三步是改革的核心,即确立重点大学和重点学校(1978年);第四步是任命在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上起示范和引领作用的特级教师(1978年),开展教育改革的实验;而第五步则是研究和建设课程与教材(1977、1978年开始)。
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到10年后的1988年末,中国制定了教学大纲(初审稿),编撰了124种教材,于1990年开始试用。1991年又作修改,1992年完成教材审查,1993年教材全面推广使用,由此一步步推进了教育变革。上海的国际研讨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为确立新的发展方向而作为改革的一环召开的。在上海纪念课程改革30周年的今天,我也来回顾我眼中的三十年课程改革。
1. 1988年的改革
那么1988年当时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从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几方面来回顾一下吧。
首先,在国家层面,学科课程结构发生了变革。第一是改变了工具学科(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类学科(政治、经济、地理、思想品德)、理科类学科(物理、化学、生理、卫生)、艺术类学科(音乐、美术、体育)的课时比例。随着工具学科和理科的比例的增加,文科的比例逐渐减少,文科和理科的比例出现了逆转。这是出于尽早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例如,从1990年的6年制中学《教学大纲》的课时分配比例来看,除“农业技术”课外,这四类学科分别占比50.8%、14.9%、19.9%、10.0%。对于理科的重视也存在特例,如浙江省提出了重视文科的方案,文科的比例为18.1%—17.7%,而理科比例只有13.0%—12.8%。第二,如浙江省的举措所显示的,《教学大纲》的标准增加了弹性,各地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样化的改革得到了认可。在小学的《教学大纲》中,城市和农村学校的课时分配有了区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5、6年级可以开设每周三课时的外语课。第三,小学1、2年级学生每周都设1课时的“游戏”时间,在高中2、3年级设4课时的选修课,这也是令人瞩目的改革举措。第四,在小学4到6年级开设每周一课时的“劳动课”,初中开设为期两周(每天4课时)、高中开设为期4周(每天6课时)的“劳动技术课”,充分体现了重视劳动生产的时代印记。
上海作为发达地区,早在那个时期就开始积极地推进课程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以升学为中心的课程进行反思,并开始重视职业教育。初中增设“劳动技术”课程,高中增设“职业指导”课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开设“简易会记”、“简易测量”、“电工技术”、“家畜饲养”、“绘画”、“家政”等课程作为“选修课程”。另外,小学还设置了“生活与劳动”课程。这种使孩子们感受“生活”魅力的课程,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与此处的“劳动”不同,日本自1970年代后期,以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为基础的综合学习和课题学习也开始盛行。1989年,小学1、2年级废除了“社会”和“理科”,新设“生活科”。)
第二,选修科目”延长到更多年级,内容也变得多样。初二、初三增加到周2—3节课,高一、高二增加到4—6节,而高三则增加到12节。
第三,虽然国家标准并未规定,但学校还是会设置一定的“课外活动”时间供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班队活动、社团活动、读书活动和自习等。其中初中设有10—12课时,高中设有6—8课时。
第四,出现了综合性学科。在中国,社会科最早是在1923年开设的。而这个时期,在国家规定的课程中,社会类学科有小学5年级的地理课,6年级的历史课,以及中学的政治、地理、历史三科,这些学科都分科开设。但是,也有一些学校却在小学3—5年级开设了“社会”,6年级开设“地理”;初中既有分科型,又有综合型“社会”。科学课程亦是如此,小学1—5年级设有“自然”,到中学,既有设分科课程的,又有设综合课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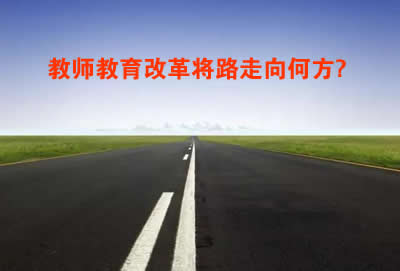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