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展望 作者: 郭华 已有0人评论 2019/9/11 16:26:11 加入收藏
导读:站在课程研究的百年之巅,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是极具课程意味的有意义的活动。百年课程研究史几乎可以看作是课程改革史或课程重建史。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出现,向课程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也进一步突显了课程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预见,未来的课程研究将进一步向宏观扩展,“关于课程的研究”将成为“课程研究”的一部分,微观研究则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实证的方法将越来越受重视,而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将真正显现。
谈到课程研究,如果不加细分,通常包含“关于课程的研究”和“课程研究”两大板块。类似“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便属于“关于课程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理论的、理念的、抽象的、宏观的,是“关于课程”的一般理论或基础理论研究,它虽不把课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却深刻影响着课程编制和课程研究的实践。这类研究与教育史一样古老而悠久,只要有教育,就有要教的内容,就会有这样的讨论和研究。与“关于课程的研究”不同,“课程研究”则以课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课程内容的选择、经验的提供以及对内容、经验的组织、加工、实施、评价等,目的是为课程编制服务,促进课程发展,形成课程理论。这类研究通常是具体的、技术的、操作性的。它的历史并不长,从1918年博比特出版《课程》一书算起,至今百年历史。我们所说的“课程研究百年”,指的就是这类研究。
课程研究百年与中国课程改革开放40年的课程研究一样,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有成就也有遗憾。带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识与感悟,于课程研究百年之巅,回望来时路、想象未来景象,特别具有课程意涵,即从历史来,往未来去,责任巨大。当回望、想象,在剧变时代下发生,困惑、焦虑、不确定尤甚,也更有意义。
虽然在急剧变化的“未来已来”时代,有着诸多不确定,但依我们对教育、对学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解与认识,关于未来课程及课程研究也能够想象一二。
一、课程研究的重要性将越发凸显
百年课程研究史,几乎可以看作是课程改革史或者课程重建史。课程研究的每一次新进展,无论是课程编制理论的进步还是新的课程体系的编制实践,都是对以前课程的改革,是新的课程的重建。这些改革和重建与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密切相关,都能从那里找到根源。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课程研究,也同样有时代的根源与印记。智能时代的到来,越发突显出课程研究的重要性。
(一)回应时代变革
1918年出版的《课程》,是课程重建的典范。博比特在《课程》前言中提到:“当今公共教育的课程(program)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更简单的状况下制订出来的。在细节上,它得到过改进。但从根本上讲,还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套本不是为今天而设计的课程被继承了下来。任何一个继承下来的体系,在它那个时代都曾是好的,但如果时过境迁还拿来使用,终究会阻碍社会的进程。这样一套体系,倘若没有从根本上就其方案和目的加以改善,只是在细节上有所改进,那是不够的。”[1]显然,在博比特这里,时代变化是课程改革或重建的根本动因,细节上的修补、改进与精致,不足以满足新时代的要求,必须做根本的变革才能回应时代的挑战,因此,要有全新的课程。“新的任务就摆在我们面前。它需要的是新方法、新教材、新视野。”[2]促成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面世的“八年研究”,源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一些严重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对课程研究者提出了大胆的挑战”[3],迫切需要课程重建。20世纪70年代的“课程概念重建”运动,与之前的课程改革或课程重建一样,也是对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曲折回应。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实验与探索,正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勃勃生机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最终,这些实验与探索汇聚为2001年全面的课程改革。可以说,世界各国的每一场重要的课程改革和有影响的课程理论,都与时代变革紧密相关。
课程研究百年之时,人类社会全面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课程研究不得不做出再一次回应,再一次改革、“重建”。无论是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教育报告、“处于争论和教育改革中的课程问题——为21世纪的课程议题做准备”[4],还是OECD的“教育2030”框架[5],亦或是一些国家、地区以及研究机构研制的“面向21世纪核心素养”或“面向21世纪关键能力”,都是从课程角度对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生活或即将面临的社会生活变化做出的主动回应。可以说,课程是反映社会变化的晴雨表。无论时代如何变换,不变的是课程研究对时代要求的主动回应。
问题在于:课程要反映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这势必会走在时代的后面、落后于时代,但课程设计与规划的目的却是为未来时代培养人,因而又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超前于时代,这便构成一对相互反对又相互支撑的有张力的矛盾。对课程规划与研制来说,这对矛盾既是困难又是挑战,也正是课程研究的魅力所在。这种困难与挑战,在剧变时代,变得激烈而尖锐。过去虽远,却是“现在”由之以来的历史,必须关照、继承;未来已来,不经预测、没有准备就已到来。课程研究如何以稳定态的“过去的”内容来培养能够适应剧变时代的公民?这是摆在课程研究面前的重要问题。
(二)探索课程应有的形态
博比特在20世纪初就感受到了社会剧变:“社会秩序的演变一直在以极快的甚至递增的速度推进着。简单的情形正日益趋复杂。”[6]……21世纪初的现在,互联网全面覆盖,智能时代已成现实,我们身处的社会正以细胞裂变的速度疾速演变着,情形更为复杂而且瞬息万变。新的科学技术进步在带来福祉的同时也造成了困扰和焦虑。人们困扰:在互联网覆盖世界每个角落、智能穿戴设备广泛应用甚至芯片植入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还需要课程、教学、教师吗?还需要课程编制、内容选择、经验提供吗?终极问题是:还需要课程研究吗?
事实上,“课程还需要吗”这样的问题,真正问的是“什么样的课程”不再被需要。那种仅仅指向知识结论的、静态的、程式化的课程,在智能时代,似乎是可以被机器替代而不再被需要了。但如此简单粗暴的排他式回答,并不能回答智能时代背景下课程对人的发展是否依然具有意义的提问,因此,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不能被替代的课程有什么特征,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正需要课程研究来揭示。
上世纪70年代,终身学习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并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学者们从人本身的未完成特性论证了它的必要性:“人……的生存是一个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点主要就是由于他的未完成性。事实上,他必须从他的环境中不断地学习那些自然和本能所没有赋予他的生存技术。为了求生存和求发展,他不得不继续学习。”[7]这种源于人自身特点的未完成性,由于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而变得越来越突出,要求教育必须做出回应。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教育变革,在迅速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正显现出它清晰的模样,那就是:“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虽然一个人正在不断地受教育,但他越来越不成为对象,而越来越成为主体了。……他是依靠征服知识而获得教育的。这样,他便成了他所获得的知识的最高主人,而不是消极的知识接受者。”[8]这一段话明确言明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即: 人正是“依靠征服知识而获得教育的”。对于课程设计而言,无论是设计分科、综合还是活动课程,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完成性、确定性、终结性、完美性的人类认识成果,转变为能够体现知识发现及发展的未完成性、争议性、开放性的课程,从学生操作、思考、发现“知识”的角度来编制和组织课程内容与经验,从人的成长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课程、组织课程,从而使课程自觉具备让学生个体有“征服知识”的活动机会。这样的课程编制思想,在百年前的博比特那里就有。他说:“教育的一项职能就是训练每一个公民,无论男女,但不是为了那些关于公民生活的知识,而是为了让他们娴熟于公民生活;不是为了那些卫生学方面的知识,而是使他们有能力保持强壮健康的体魄;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抽象的科学知识,更是要让他们在把控现实情形时有效地运用这些思想。”[9]这样的思想,就包含着从培养人、形成人的角度进行课程设计的思想。这样的课程设计思想,在智能化时代尤为重要,借用马云的话说,在机器变成人的时代,学校如果还把人变成机器,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智能化时代提醒我们,学校课程不能把人变成存储知识和信息的精致机器(如果这样,人永远比不过智能机器),也不能让学生止于识记、模仿、继承,而要激发、引导、培育学生的想象力、思考力和创造能力,虽然识记、模仿、继承本身依然有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课程,须以未完成的、开放的、可质疑的形态出现。
在信息时代,知识(信息)以爆炸的速度扑面而来,以前人们“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的情形变化了。只要愿意,“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再无“饥饿”之苦。因此,课程不应只是知识的载体,而是要有“百度”所不具备的、能够引发学生反思、探究、建构的内在神蕴并以双重形态呈现:即完成与未完成、完美与可质疑、终结与开放,等等。
“完成”“完美”与“终结”,是指课程内容必须提供人类认识的最高认识水平,目的是使学生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营养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把人类的成就变成自己的血肉与骨骼;打开眼界,提升境界;更好地理解世界与自我。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来说是一把钥匙”,只有站在最高成就处,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以及历史的意义。
“未完成”“可质疑”与“开放性”,则是指课程要为学生的主动探索活动留有空间,引导学生回溯历史、把握知识的基本形态、来龙去脉以及价值追求;帮助学生理解前人在知识发现、探索、建构知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自觉评价前人的努力,思考另一种可能的建构方式、想象可能有的结果;引导学生意识到“此时此刻”的终极水平的知识是历代先贤持续探索、主动建构的结果,因而是“临时的”,在发现新知识、推进人类认识水平提升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发现者,每个人都可能是推动者。这样的课程,意在缩短学生与知识的心理距离,能够增强学生发现、建构知识的意识、能力、自信心与使命感。
当课程具备足够的未完成性、开放性、可质疑性时,课程才有足够的空间和可能去引导学生亲切体会知识的魅力、感受前人在知识发现、探索、建构知识过程中的艰辛、努力和贡献;激发、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引导学生进行理性的、审慎的审辨活动,在探索、批判、质疑中去辨别知识的“真伪”“美丑”,主动“建构”具有“真”“美”特性的“完成形态”的知识;增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与意识,帮助学生从“历史”走向“未来”,形成能够承担创造未来的意识与能力。
这样的课程,本应是课程应有的样子,只是以前被遮蔽了;由于智能时代的挑战,它的样子才清晰地显现出来。
我们想象并期待:如此形态的课程内容与经验,能够应对快速发展的智能化时代的挑战,能够引导学生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茫然等待不确定的未来社会的冲击。对于课程而言,只有把知识变为创新的基础,才能彰显知识的价值、才是真正的课程;对于学生而言,只有成为主体,才是真正的学习者。正如《学会生存》所言:“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个问题。”[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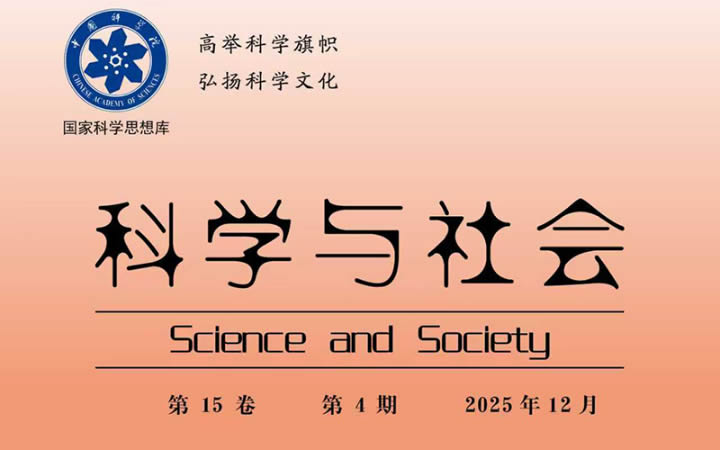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