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 市川博 已有0人评论 2019/3/5 8:54:51 加入收藏
导读:市川博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前身),历任大阪府立大学、东京教育大学助教,横浜国立大学、帝京大学教授。市川博教授早年研究近现代中国教育史,是日本研究中国教育的主要代表,曾于1964年被选拔为最年轻的访华团成员,随第一个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机构邀请的日本学术访华团来访。市川博同时从事社会科教育论、课程论与教学论研究,担任过日本社会科教育学会会长、日本教育学会秘书长,以及日本教师教育学会、日本课程学会的常任理事。他致力于中日两国的教育交流,指导过众多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20世纪90年代被华东师范大学授予顾问教授、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授予课改委员会顾问,为推进中日两国的教育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推进了华东师大与横滨国立大学之间的合作交流。值此中国课改40周年之际,市川博撰文回忆他研究中国教育以及亲眼目睹的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程,并表达对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期待。
我出生于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之后,即1937年8月,今年80岁。从我开始致力于中国教育研究至今正好60年,这60年中的后30年,中国发生了巨变,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大国之一,教育事业也获得飞速发展。我有幸目睹、亲历这一变化,并与中国的教育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与广泛的合作交流关系。值此中国课改40周年之际,我特撰写此文,回顾我所见到的中国教育、尤其是上海教育的发展变化,并表达我的感想和期待。
一、与中国相遇
(一)从高中时期与朋友的读书会到对中国的研究
我于1944年上小学,当时接受的教育是要成为军国少年去打败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敌人。但是一年半以后,日本宣告战败,开始反思军国主义的灌输式教育,推行以建设民主与和平的国家为目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新教育尊重儿童的兴趣,倡导儿童通过自主探究自身感到迫切性的问题,培养能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我进入东京教育大学,师从新教育的倡导者长坂端午教授(战后第一个学习指导要领的主要制定者),受其影响,我认为新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就是教育的核心,于是致力于研究欧美新教育。
上大学后,每月我都会和高中时期的朋友在我家开一次读书会,每个月选一本书阅读。参加读书会的朋友来自法律、经济、历史、社会、教育和医学等多种专业。在大学二年级(1958年)时,为了加深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对于当时正开始进行人民公社运动的中国,我们开展了各种调查与报告活动。我负责了有关中国教育的调查与报告。
在中国那些教育无法普及的地区,民众自己创办了“民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在学校学习对自己的生活和生产而言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我对中国这样的新尝试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决定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教育。然而,我的决定遭到了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强烈反对。战后的日本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在国内推行反华政策,且与美国缔结日美安保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来共同对抗中国。在那种时候,如果对中国抱有好感从事中国研究的话,会被当做思想危险分子,很难找到工作。尤其是,要想成为中国教育研究者在大学任职,会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是,长坂先生却鼓励了我,他说:“今后中国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我们大学需要至少一名研究中国教育的研究者。如果研究得出色的话,肯定会有人关注的。”还有其他老师也给了我勇气,我想:“如果不结婚,自己一个人的话,是能活下去的吧,”于是我下定了研究中国教育的决心。
就这样,我完成了以《人民公社时期的教育改革》为题的本科论文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教育的变迁》为题的硕士论文。幸运的是,基于上述学位论文而撰写的论文,前者在博士一年级时被收录进梅根、安藤主编的《现代教育改革》(东洋馆出版社,1963年出版),后者在第二年被收录进长坂主编的《现代历史教育》(葵书房,1964年),并作为单行本得以发行。
(二)最初的中国访问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64年。当时出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要访问当时还未恢复邦交的“敌国”,更是障碍重重(有过中国入境纪录的人会被美国和中国台湾拒签)。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希望加强与中国友好关系的研究者、学生和日中友好协会成员等民间人士一同发起了邀请中国大学研究者的运动。终于在1963年成功邀请到了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为了不让中国代表遭受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暴徒的袭击,我们在代表团住宿的酒店楼层入口处设置了关卡,轮流彻夜警戒。召开学术友好交流集会的时候当然也配备了警备人员。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东至东北大学,西至九州大学都举行了气氛热烈的中日交流活动。
第二年,中国科学院发出了邀请日本学术代表团访华的信函。最后来自邀请过中国访问团和举办过日中交流活动的地区的9位教授组成了日本学术代表团,于1964年10月到华访问。这9位教授分别来自经济、历史、文学、语言、教育、物理、生物学等领域(其中两位后来被选为大学校长,都是具有很高声望和学识的人)。当时我还是博二研究生,有幸作为随行人员前往中国。
我们代表团经香港到达广州、北京、西安、延安、成都、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受到了一个月真挚热情的接待。在进行学术访问的同时,我们还走访了发展中的农村和工厂,以及名胜古迹,开拓了眼界。我们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接见;在北京停留期间,还得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研制的消息,我们作为代表团发表的祝贺声明被刊登在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停留中国期间去中小学观摩课堂教学,但我们拍摄了学术交流和中国发展情况的照片。由于当时的日本很难获得关于中国既新又准确的信息,所以访华团成员接到了来自多方的请求,开展了多场报告会。针对教育学研究者,我和小川太郎教授一起在东京大学举办的报告会上,做了关于教育领域日中学术交流成果和中国教育动向的报告。
二、我的研究生涯——从中国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起源研究到日本教学实践研究
(一)对中国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起源的研究
我曾一直以为,如果日本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话,我就无法成为大学教师。不过,在我升入博三不久,我便获得了一个职位,前往大阪府立大学任教。三年后,我回到母校东京教育大学任职,四年后(因反对东京教育大学改组为筑波大学)来到了横滨国立大学。在我调动工作的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我受邀前往庆祝邦交的宴会,亲眼目睹了演讲台上邓小平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的拥抱,感受到时代的巨变。
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动荡期,我撰写了有关那一时期教育改革的论文,并刊登在教育期刊和《新中国年鉴》上。另一方面,我开始研究现在中国广为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起源,梳理了倡导儿童中心主义的新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919年日本开始推行儿童中心主义教育,2月杜威夫妇到访日本。
在曾于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新教育熏陶的陶行知和胡适等人的强烈邀请下,杜威夫妇于5月1日从日本抵达上海。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杜威多次写信寄给自己的孩子,详细叙述了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状况。杜威夫妇原来只打算在中国停留几周时间,但最终在中国待了两年零两个月。杜威夫妇北起沈阳,南至广东,在中国11个省进行巡回演说,积极倡导尊重孩子的个性、以孩子切实的兴趣和生活为基础的新教育理论。
杜威回国后,他的弟子克伯屈(Kilpatrick)访问了中国,积极倡导由儿童自发地制定计划来解决问题的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同是杜威弟子的帕克赫斯特(Parkhust)也来到中国,提倡要摈弃同步教学法,倡导道尔顿制(Dolton plan),即让学生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开展个别学习,而教师只是提供建议。就这样,相继有教育学者由美国访问中国,为中国的新教育做出了贡献。(关于新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本文因篇幅有限只能割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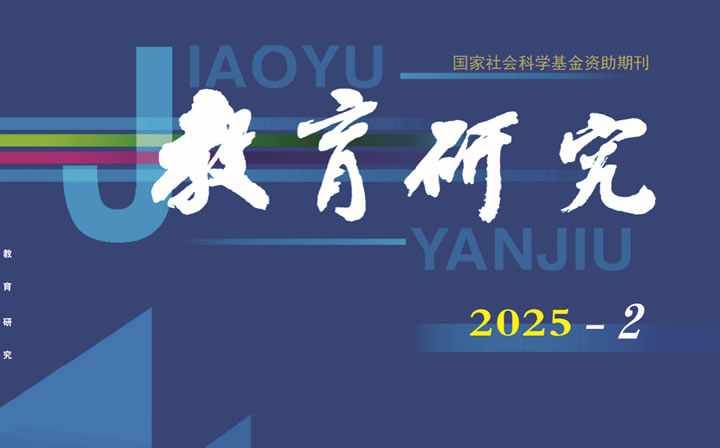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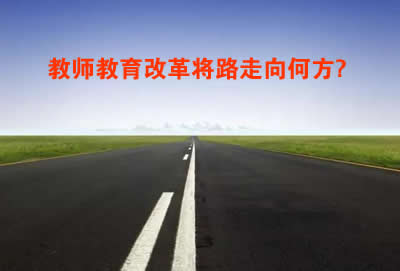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