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识分子 作者: 钟晓慧 已有0人评论 2020/6/1 11:13:29 加入收藏
当人口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儿童教育及发展日益成为新世纪全球关心的议题时,许多学者对中国儿童照顾展开研究。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作为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承受巨大的照顾压力。这种困境与我国缺乏对普通家庭儿童照顾的家庭政策及支持性服务有关;同时,转型期家庭规模小型化、关系多样化,人口流动增加,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儿童照顾精细化也加剧了照顾资源的紧张。大量研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祖辈发展出代际合作育儿(下称隔代抚养)方式。张聪、冯文等学者(2020)将两家人、两代人的合作互动视作年轻夫妻为了最大化资源而采取的一种功利性策略(utilitarian strategy)。
隔代抚养在我国农村和城镇均十分普遍。《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指出,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即便3岁以后儿童上幼儿园,由祖辈直接抚养的比例也有约40%。Ko和Hank(2014)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08年数据,发现58%的中国老年人曾经帮忙照顾过成年子女的孩子。2014年,中国老龄中心的全国城乡调查数据显示,该比例上升至66.47%;其中,(外)祖母照顾孙辈占70%左右。可见,隔代抚养成为我国家庭跨地域、跨阶层的儿童照顾主要模式。
一、长寿社会的全球现象
尽管祖辈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隔代抚养的研究近年来也明显增加,但是目前研究更多采用一种“朝下”的视角。它们从父母(尤其是母亲)或者儿童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祖辈自身感受和经验出发,来探讨老年人的角色与作用,动机与行为,以及隔代抚养对老年人晚年生活影响,以及社会政策的意涵等问题。在隔代抚养和儿童照料研究议题上,祖辈主体性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把老年人提供隔代照顾看作是家庭义务,甚至还存在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习俗,老年人也很享受天伦之乐。换句话,老人带孩子不仅约定俗成,是应该做的,他们也能从中获得好处。这些刻板印象阻碍了我们对该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国际比较。
要破除 “隔代抚养是中国社会特有现象” 这个条框,我们不妨将其放在更大的尺度上。牛津大学社会政策系 Buchanan 教授在2018年特刊卷首语《二十一世纪的祖辈》(Twenty-first century grandparents)中指出,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的祖辈在抚养教育孙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作用。根据《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数据,2004年欧洲大陆58%的(外)祖母和49%的(外)祖父参与照料15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Craig 和 Jenkins(2016)根据2006年澳大利亚统计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Time Use Survey)发现,约60%的澳大利亚受访祖辈表示他们参与照料孙辈。即便在美国,Guzman(2004)年根据1992-1994年两项大型全国性调查数据(NSFH 和 NHES)发现,47%的美国祖辈参与儿童照料,这个比例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有大幅度提升,表现在祖辈与孙辈同住数量激增。即便在中国,祖辈普遍参与儿童养育,成为仅次于母亲的主要照料者,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Chen, Short & Entwisle, 2000)。由此可知,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这是一种全球现象。
Buchanan认为,这种全球趋同现象与人类寿命更长、低生育、家庭关系剧变等人口变动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老年人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世界卫生统计2018》报告指出,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2000年66.5岁提高至2018年72岁。祖辈与子女、孙辈共享生命的时间拉长,也更有能力照顾孙辈。另一方面,全球生育率逐步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到2017年,全球总和生育率由4.979下降到2.432。以中国为例,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显示,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05。每个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孩子对家庭和社会而言变得更为珍贵,祖辈更有可能、也更愿意以参与照料来投资于儿童。此外,全球家庭关系激烈变动,也成为催化剂。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女性劳参率提升,以及工作全球化引发的人口流动,也增加儿童失养失教的风险。这三方面变化都促使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
二、真正的 “无名英雄”
祖辈们不仅为孙辈付出照顾服务,并且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资助。例如,2017年国际长寿中心(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发布的报告指出,在英国有超过900万的祖辈参与孙辈照料;其中,近300万祖辈定期提供照顾,三分之二的祖辈为孙辈教育提供经济资助,花钱请保姆。英国祖辈平均每周用于照料孙辈的时间约为8小时,这远低于欧洲高强度的祖辈育儿照料时间(每周超过30个小时)。该报告还说,96%祖辈并没有从子女那里得到任何照顾报酬。相反,祖辈在照顾同时,还要支付孙辈活动花销,每年总金额高达38亿英镑。在美国,有31%的(外)祖辈每周提供少于10小时的照料,同时也有33%照料时间超过30个小时。
中国的情况类似,Wang 和 Gonzales(2019)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发现,参与隔代抚养的祖辈中,近一半(46%)老年人为孙辈提供平均每天8个小时的照顾。换句话,每周至少超过40个小时。他们的研究指出,照料孙辈的强度和时间与祖辈的抑郁症有关系。许多研究也表明,照料孙辈的中国老年人的个人睡眠时间被压缩,休闲时间变得零碎,社交活动机会也明显减少。除此之外,精神压力和体力负担较大,有时候还需要补贴子女的生活开支。这种压力在三代人共同居住、低收入或者由外婆带孙辈的家庭尤为常见。因此,中国参与儿童照料的祖辈不仅在老年总人口占比高,而且照料时间长、强度大。
世界各国隔代抚养的差异性,是特定制度条件、文化规则,以及家庭情况形塑的结果。例如,Igel 和 Szydlik(2011)基于 SHARE 数据发现,与惯常认知不同,南欧祖辈照顾孙辈的参与度较低,但强度较高;而北欧的祖辈照顾孙辈参与度较高,但强度较低。他们认为,北欧国家由公共机构提供稳定的、长时间的托幼服务,降低了“祖辈照料孙辈”的强度,祖辈只需要偶尔提供照顾,反而鼓励了更多老人参与带孙辈。相反,南欧国家的托幼服务非常有限,照顾孩子成了家庭尤其是祖辈的义务,老年人的压力很大,不愿意做这件苦差事。换句话说,家庭投入与国家福利制度在儿童照顾上相互补充,但是普惠式的托幼服务如果长期匮乏,会大大削弱祖辈参与育儿的意愿。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出现类似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公办幼儿园和托儿所停办,同时国家鼓励市场兴办私立幼儿园和早教机构,收费非常昂贵。Zhen Cong 和 Silverstein(2013)根据2001年至2009年追踪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祖辈非全职照料孙子的比例下降,全职照料比例则有所上升。他们认为,这种变化不仅与经济增长、父母外出务工模式的变化、生育率降低有关,也与九十年代国家大幅度减少公办托幼服务、家庭承接育儿责任密切相连。在过去二十年,随着国家退出普通家庭的儿童照料责任,祖辈参与儿童照顾的比例和照料强度逐渐增加。但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一些学者观察到,不少曾经带过一孩的祖辈(尤其是外/祖母)不愿意再带二孩。这出现与南欧相似的趋势。祖辈参与儿童照料的意愿降低,这种情况有多大比例呢?需要进一步研究。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母系祖辈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孙辈照料。Ko 和 Hank(2014)比较2008年中韩两国隔代抚养的相关数据发现,韩国祖辈更愿意照顾(就业)女儿的孩子,而不是儿子的孩子;而中国祖辈没有表现出这种特点。他们认为,父系传统的重要性在韩国开始逐步下降,即祖辈更多基于子女及孙辈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帮助,尤其是就业的女儿。但是,张聪、冯文等学者(2020)基于对南京77个家庭追踪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祖辈们正在摆脱父系传统,转而根据具体情况(譬如,祖辈与子女/其配偶的关系、自身照顾能力、子女是否需要人帮忙等)来提供照顾。这促使更多外祖辈,尤其是外祖母参与照顾孙辈。Baker 等学者(2012)比较中国农村祖辈和美国祖辈在隔代抚养的角色时认为,美国祖辈倾向于对中间一代的危机(例如忽视、虐待等)进行干预,他们扮演 “儿童拯救者”(child savers);而中国农村祖辈是为了实现家庭更大的经济目标,化解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提高其经济生产力,他们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者”。换句话,对于城市和农村祖辈而言,为子女(包括女儿)更好安心工作,提高家庭整体利益,是他们参与儿童照料的重要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祖辈这一庞大的儿童照料群体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用自己的时间无偿地照顾孙辈,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中青年一代不可能有如此高的经济生产力,国家也不可能节省巨额的托幼服务开支。用 Buchanan、Baker 等学者的话来概括,这群祖辈是真正的 “无名英雄”(unsung heroes)。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照顾付出需要得到社会及国家的承认,长期缺位的家庭政策应该尽快完善,给予他们充分支持。
参考文献
Buchanan, A., & Rotkirch, A. (2018). Twenty-first century grandparent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anging roles and consequences.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13(2),131-144
Hank, K., & Buber, I. (2009).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2004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0(1), 53-73.
Craig, L., & Jenkins, B. (2016).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in Australia: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lates of providing regular grandparental care while parents work. Community, Work & Family, 19(3), 281-301.
Guzman, L. (2004). Grandma and Grandpa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Patterns of Involvement. Child Trends Research Brief. Child Trends. 4301 Connecticut Ave NW, Suite 100, Washington DC 20008.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2017). The Grandparent Arm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lcuk.org.uk/index.php/publications/publication_details/the_grandparents_army
Baker, L., Silverstein, M., Arber, S., & Timonen, V. (2012). The wellbeing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orary grandparents: Chang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global contexts, 51-70.
Igel, C., & Szydlik, M. (2011). Grandchild care and welfare state arrangements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1(3), 210-224.
Ko. P. C., Hank. K. (2014).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and Korea: Findings from CHARLS and KLoSA.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9(4), 646-651.
(钟晓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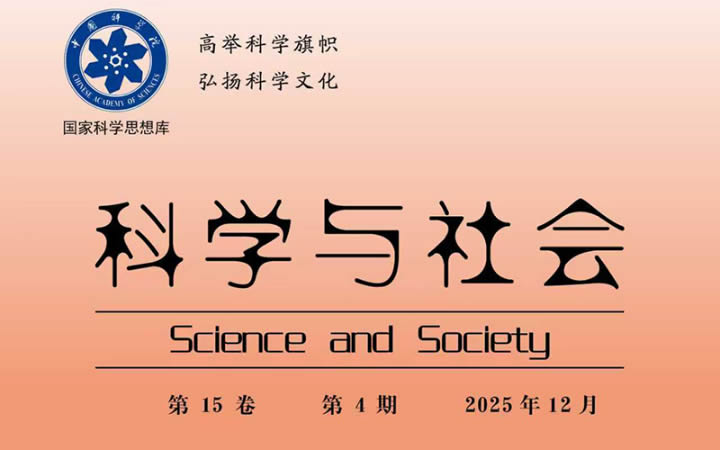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