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科学 作者: 崔允漷 已有0人评论 2020/5/22 14:39:15 加入收藏
导读:
2020年春季,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线教学维持着数以亿计的大中小学生和教师们的“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对稳定学校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后,在线教学是完成了历史任务后“功成身退”还是“升级改造”后进入可持续性发展?
继“战疫中的课程思考”系列之后,课程所崔允漷教授领衔团队在核心期刊《教育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对疫情下的在线教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能为后疫情时期及疫情以后在线教学的发展提供思考与借鉴。
2020年的春天有点乱。全国14亿人口无一例外在忙“战疫”,其中近半数人口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又要“对付”网课。这场突如其来的在线教学打乱了所有教育从业者、大中小学生及学生家长的生活。一不小心上了线,校长成主导、教师成主播、家长成主管、孩子成了手机的主人……有些技术专家似乎逮到了机会,到处宣称疫情将中小学教学推向了“在线”,疫情带来了教育的未来。这是真的吗?
一、技术专家的教育预言有鼓动意义,但并非都会应验
技术对教学的冲击这一话题由来已久。每当技术取得某种标志性的进展时,就会有大咖出声:教师要被取代,学校即将消失……我们已经听过太多这方面的旧闻了。
早在1910年,当爱迪生(T.Edison)发明出活动胶片投影机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帮助教师将物理、化学等教学内容改编成电影,并在学校里使用。有了这点尝试,他在1913年7月接受《纽约戏剧镜报》专访时就大胆预言:
学校里用的书很快就会过时,学生可以通过看电影来接受教育。借用电影教授人类知识的每一个分支是可能的。在未来10年内,我们的学校制度将会被彻底地改变。[1]
不知是因为爱迪生名扬天下,还是这句预言过于惊世骇俗,此话一出,各种回应持续不断,褒贬不一,有人信以为真,也有人嗤之以鼻,甚至还拿来当嘲讽,主流媒体反复转载,成了一个跨时段的社会议题,甚至70多年后还有人想起这句豪情满满的预言。1986年1月31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涉及大学教育未来的文章,作者直接引用了爱迪生的预言,然后评论道:(至今)已经过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学校在用的这本书依然没有过时,大多数学校主要还是依靠“站着的教师给整班坐着的学生讲课”。作者告诫人们,当我们怀抱大学教育未来的所有梦想时,我们决不能低估教师的变革阻力。
更有趣的是,爱迪生预言百年之际,2012年2月,美国联邦教育部长和通信委员会主席在一次演讲时大谈数字技术在教育中将会有更广泛的应用,每个小学生都应该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教科书将成为过去。针对此番言论,《洛杉矶时报》又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把高科技设备放在教室里究竟谁在受益?》。作者带着质疑的口吻说道:“我老早就听人说过,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找到了。‘学校里用的书本很快就会过时……在未来10年内,我们的学校制度将会被彻底地改变。’只是当时借以预言的革命性技术是电影,而不是现在的互联网或笔记本电脑。”[2]作者拿爱迪生这句众人皆知且没有实现的预言,告诫美国联邦教育部长和通信委员会主席不要信口开河,轻易提出不怎么靠谱的新预言。
笔者还想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信奉行为主义心理学,为了追求教学效率,有一帮专家非常热衷于研究和运用教学机器,其核心理念就是想让教学机器替代教师。同时,美国正在策动一场要与苏联抗衡的课程改革,怀着“伊凡能行,约翰怎么可以不行”的壮志,组建顶级的专家团队,并邀请一些能代表最前沿研究的专家培训这批国家课程改革的领导者。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拉姆斯丹(A.A.Lumsdain)就是受邀的专家之一。他以研究教学机器闻名,因此他负责培训的主题也是教学机器。这位大咖,在1960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自动化应用于教学过程会带来哪些可能? ……将教师指导或调节学生学习过程的各种功能加以编码,以便在时间和空间上能被替代或延伸,必要时加以复制。”[3]这种希望通过机器而不是教师来提高教学效率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影响了美国这场“防教师”的课程改革。但是结果如何呢? 约10年后,教育改革的灵魂人物、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纳不得不承认这场课程改革“当时实在是‘天真无知’……过于理想主义了”。[4]
笔者与大家分享这两个例子,并不是想做事后诸葛亮,也不是要为悲观主义者或守旧主义者代言。这样做只是想分享自己的一点感悟:学校教育的变革是一种系统的而不是单因素的变革,是一个渐变而不是突变的过程。任何宣称某一个影响因素在某时就会彻底改变学校教育的预言,都存在极大的风险。要回答在线教学是不是教育的未来,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于教师与课堂。学校教育只有到了不需要或失去了课堂的时候,教师的身份或角色才会改变。试想,我国目前开展的在线教学到底是课堂的消失,还是课堂的转移? 如果课堂只是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那么在线教学依然还是一个梦。疫情结束,“涛声”依旧!
二、芬兰的在线教学不是意外,技术难以直接创造艺术
如果没有OECD 的PISA 测试,那芬兰这个北欧小国一定不会引起如此众多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教育人士注意。芬兰在21世纪初进行的PISA 测试中连续两次获得第一,这一成绩让世人惊讶。其学校教育被美国学者尊称为“具有高绩效的教育系统之一”,吸引国人接连飞越西伯利亚,去一个与中国国情有天壤之别的国家取经。然而,你是否知道芬兰在应对此次疫情的在线教学情况?

芬兰早在2009年就已成为全球首个立法规定全民享有宽频上网权利的国家,甚至还限定了最低网速。[5]目前,芬兰人口上网比例已达95%(2019年6月的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上网比例是61.2%),是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17年,16岁以上人群中平均每人有3.2台可以上网的电子工具。按理说,和其他国家相比,芬兰在线学习的条件应该占了很大的硬件优势。然而,在这次疫情导致的“停课不停学”面前,芬兰学校在应用信息科技方面的状况,或多或少有点出人意料。
尽管人们公认芬兰的教育理念引领世界,但在芬兰的课堂中很难找到时髦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连电脑也不多。芬兰教育界普遍认为,对学生而言,输入的信息量愈少愈好,学生极为有限的注意力与其浪费在电脑输出的模拟信号上,还不如交给面对面的教师。因此,芬兰目前仍有不少一至九年级的教室里没有配置电脑设备,很多学校没有提供网上个人帐户或网上学习平台。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3月17日芬兰开始全国停课后,大多数学校推行在家学习模式,仍是要求学生根据书本和作业单学习。只有少数学校有完整的网上课程,进行在线教学,让学生上网自主学习。即便是在线教学,学生也无法与教师、同伴沟通讨论,教师也无法即时提供评语反馈。芬兰过去都不鼓励(甚至禁止)给学生布置作业,教师也习惯了每天工作四小时,采用跨学科、以主题为中心的整合式教学,强调师生互动和建构学习等模式,所有这些惯常做法却成了在线教学的障碍。首都赫尔辛基有一所颇具名气的国际学校,在国家宣布停课后用了三天时间紧急搭建了学校的在线学习平台,花两天时间仓促培训教师如何布置学生的在家学习,还没有像我们那样让教师仓促上马当“主播”,现在该校成了芬兰少数提供网络平台的学校之一。
这就是“高绩效教育系统”标杆的芬兰在线教学现状,是不是让你感到意外? 笔者并不是想推崇也非贬抑芬兰经验,而是想讨论在实验室里发生的科技革命能否推广到普通课堂的问题。在线教学发展了20多年,有控制的个别班级或学校或许取得过成功,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开展在线教学取得成功的先例;“线上见”与“面对面”各有优势,混合学习才是未来的方向。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W.James)告诫人们,科学实验室离真实的课堂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说不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我们不怀疑大多数科技专家的积极动机或良好愿望,学校教育也非常需要探索性、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但千万不要过于夸大在实验室中得出的结论,不要过度推论有控制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三、“在线教学”若要保证“在学习、真学习”,学习动机是关键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无论你愿还是不愿,反正让我国近一半国人卷入的在线教学都已存在! 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一定会给很多人特别是科技专家带来关于未来教育的无限想象。笔者无意预测学校教育的未来,只在意在线教学是否更好地解决了学生“在学习、真学习”的问题。因为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只要“让更多的学生投入学习,让每位学生经历真实的学习”,尽量减少“不学习、无学习、假学习”的现象,都是教育变革的价值追求。
关于动机研究的最新进展大概是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6]该理论超越了“把人当作行为”的假设,而是“把人作为理性的人”,整合了归因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基于人本主义,建构了人的三种内在需要:胜任、关系和自主。
“胜任需要”包括学习者如何实现某些目标的知识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技能,相当于自我效能中的“我能行”;
“关系需要”是与同龄人、教师和家长建立安全和满意关系的内在要求,相当于个体在一定的群体中“我要行”;
“自主需要”指的是发起和规范自己行为的能力,相当于将成功归因于努力的“我可行”。
自我决定理论从三个维度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在动机框架,为我们设计学习动机提供了理论依据。
凯勒(J.M.Keller)致力于在线学习动机设计研究20多年,提出了ARCS动机设计模型。[7]该模型利用颜色、风格、声音、幽默、新奇、互动和参与等感性的内容引起学生注意(Attention),并把要学生学的内容与学生个人的需求建立关联(Relevance),然后将学习的难度与进度调整到适合的程度以使学生在学习成功中增强自信(Confidence),以及通过自然后果、意外奖励、避免负面影响、强化计划等方法使学生获得满足(Satisfaction)。该模型涉及从低到高、由外而内的动机范畴,体现了归因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在在线教学中的综合应用,但没有很好地体现学习者更高级的内在需要,特别是作为理性人所特有的意志、毅力、坚强甚至反思等更高级的动机因素。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需要设计如何激发或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这让笔者想起新课程刚启动时有一句流行语:教师不要教教材,要用教材教。“用教材教”隐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清晰的目标是“用教材教”的依据和前提,没有相对统一的清晰目标,倡导“用教材教”是相当危险的;第二,“用教材教”的实质就是变“教材内容”为“教学内容”,教材内容是专家编的教科书中呈现的内容,而教学内容是经过教师处理后的、与对应的目标相匹配的内容。
如果从设计学习动机的角度看“用教材教”,其意就是让教师在处理教材时,把教材内容变成有趣、有用、有意义的教学内容。
所谓“有趣”,就是让学生在感性层面对要学或在学的内容产生愉悦感,类似凯勒提出的“引起注意”。
所谓“有用”,就是让学生发现要学的内容与自我的“需求或功利”建立关联。还需要让学习者明白要学的内容有助于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有助于自己“能行、更行、更强”,这就需要教师制定清晰、有价值且可实现的目标,让学生明白学习结果的意义。
所谓“有意义”,就是让学习者明白要学的内容最终需要超越即时的兴趣和一时的功利,转化为对自己终身学习或发展都有用的知识、能力与观念;让学生明白学习需要良好的习惯,需要自我修炼、反思,有时甚至需要毅力或意志。这就需要教师将所教的知识结构化、情境化、意义化,倡导具身学习、深度学习与累积学习,以便于化信息为知识、化知识为智慧、化智慧为德性。
基于问题或任务的教学(ProblemorProject-BasedLearning)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用一个大问题或大任务组织教学过程,把相关内容设计得有趣、有用和有意义,就会极大提高线上或线下学习的“粘度”。从动机的视角看教学内容,既体现了由外而内的设计理念,也涵盖了低级、中级与高级的动机范畴,还揭示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它是对ARCS模型和自我决定理论的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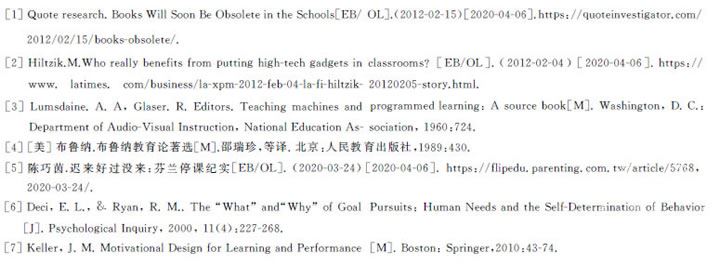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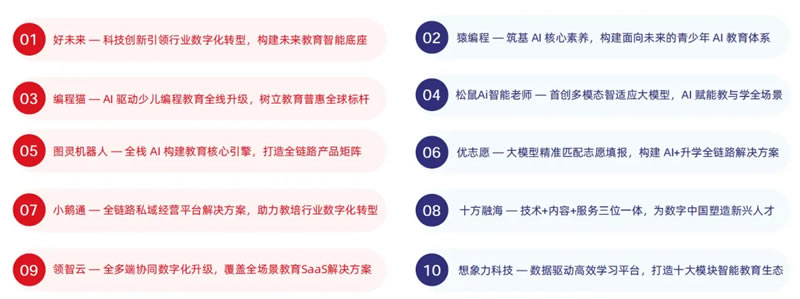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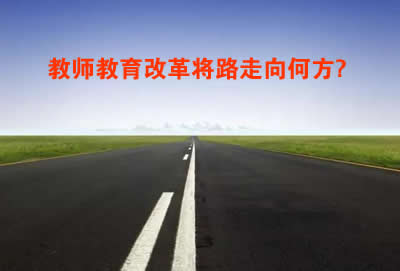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