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 刘良华 已有0人评论 2025/2/13 13:31:57 加入收藏
导读:
兴发教学是对中国古典教育教学智慧的一种理论提炼。孔子有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又云:“兴于《诗》。”“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此,兴发教学理念的原型得以显明:一方面,兴发教学乃是在充分唤起个体愤悱状态的基础上,再进行启发,以促成理智思维的通达;另一方面,兴发教学的起点乃是《诗》,《诗》之兴、观、群、怨带出个体融入周遭世界的基础性状态,使之成为个体理智思维发展的基础与准备,避免个体思维发展的无根化。由此,兴发教学不仅仅是一种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积极路径,也是探索当下学校课堂如何焕发生命活力、提升师生生命质量的可行性路径与方法,更重要的是,其间隐含着的乃是古典中国所奠定的中华文教体系的隐在结构。
早在2011年,在追叙先哲的基础上,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良华教授、彭正梅教授先后提出兴发教学理念,并做了持续性的阐发,同时连续举办全国兴发教学论坛。时至今日,兴发教学的论文、著作有如星星之火,尚待燎原,而兴发教学实践推广亦方兴而未艾。《全球教育展望》现推出“兴发教育研究”专栏,意在系统呈现兴发理念的同时,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中国教育界向来重视启发教学,即便不能付诸行动,至少普遍将启发教学作为正面的、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学模式。问题是,启发教学的重点容易被误解为教师的启发而不是学生的主动学习与主动思考。更严重的误解在于,启发教学容易被视为唯一值得关注的中国教学传统,却忽视了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的另外两个传统:一是时习教学或笃行教学;二是兴发教学。这三个新教学传统一起构成中国儒家教育学尤其是心学教育学的基本主张。孔子较早地倡导这三个传统,孟子继之并在儒家内部开创“心学”教育哲学的新支脉。遗憾的是,后人普遍重视启发教学、误解时习教学而忽视兴发教学,并一再出现以朱熹与陆九渊之争(简称“朱陆之争”)为典型的学派之争。“朱陆之争”之前有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之争(简称“孟荀之争”),“朱陆之争”之后在明代发展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宋代以来,程朱理学长期占据中国教育学的主流地位,但由于程朱理学偏重“学”而忽视“思”,偏重“知”而忽视“行”,偏重“理”而忽视“情”,积弊既久,迟早会激起以陆王心学为核心价值观点的改革风潮。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核心议题都是学思关系、知行关系和情理关系,不同之处在于,陆王心学更看重学思关系之学、知行关系之行、情理关系之情,并由此重视启发教学、时习教学和兴发教学。狭义的兴发教学主要指向情感兴发,而由于启发教学、时习教学也有兴起和引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效应,广义的兴发教学包含了情感兴发、启发教学和时习教学。
一、启发教学与学思关系
启发教学源自《论语·述而》中的一段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对这段话的一般解释是:“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1]通俗的解释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2]
这样的解释已经很明白了,问题是,这类解释只触及了先学后教的关系,却没有揭示“启发教学”背后所隐含的学思关系以及由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的改革新方向。倒是朱熹在述引程子的解释时,提示了启发教学所隐含的学思关系及其转向。“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3]
程子提示,启发教学不只是将传统的教与学的先后顺序做了调整,即将先教后学转换为先学后教。实际上,启发教学所要改革的重点在于由重视教师的教转向重视学生的自学、自悟与自得。《礼记》的说法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周易》的蒙卦则特别提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教师应该让儿童自己尝试而不必“好为人师”。儿童在尝试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惑或困难并请求帮助的时候,教师才可以相机引导。只有让学生真诚地自学、自悟与自得,学生所学的知识才会坚固可靠、沛然活泼。这样看来,启发教学的重点在于立足于学生自学、自悟与自得之“愤悱学习”。中国古典的“愤悱学习”接近现代教学论所讨论的“发现学习”或“自学辅导教学”。[4]
愤悱学习之所以重要,乃因为愤悱学习隐含了学思关系以及相关争议。惟立足于学思关系的视角,才可能透彻理解启发教学所引领的教学改革的新方向。相反,如果不将学思关系与启发教学关联起来,就很难理解启发教学的改革意图。
《论语》有两处直接讨论学思关系。一是《论语·为政》的说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提示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则败。这个说法接近康德(I.Kant)所谓“知性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5]。二是《论语·卫灵公》的说法:“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是对“思而不学则殆”的警告。
在“学而不思则罔”和“思而不学则殆”之间,孔子本人虽然以“吾尝”的自传经验表达了对“思而不学”的警惕,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仅仅强调“思而不学则殆”而不重视“学而不思则罔”。《论语》反复提示了“思”的价值或“学而不思”的后果。比如,“多闻阙疑”“闻一知十”“三思而后行”“君子有九思”(尤其是“听思聪”“疑思问”),等等。
不过,单就“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而言,确实很难判断孔子在学与思之间究竟重视“学”还是“思”。这为后来的学派之争埋下了隐患。以荀子学派(简称“荀学”)为代表的“博学派”重点发挥“思而不学则殆”的警告,而以孟子学派(思孟学派,简称“孟学”)为代表的“心思派”重点关注“学而不思则罔”的训诫。[6]
在学思关系上,荀子更重视学而不那么重视思。荀子不仅将孔子以“吾尝”提出的自传经验转述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而且直接以“劝学”为主题建构自己的教育体系,并将《劝学》作为《荀子》的首篇。所谓“劝学”,摆明了讨论的重点在于“学”而不在于“思”。荀子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也就是借助他人总结出来的书本知识或间接经验来充实自己。此处既不关注独立思考,也不讨论尝试错误的直接经验。
如果说荀子重点关注“劝学”而不那么看重“思考”,孟子则更重视孔子提醒的“学而不思则罔”,而且以“心之官则思”来证明“思”的先验可能性。《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所谓“思”,就是自求、自得。自求、自得就是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孟子·离娄下》曰:“自得之,则居之安,……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在这点上,孟子不同于孔子。孔子虽然倡导“启发”,但也乐于“诲人不倦”,不知疲倦地为他人提供教诲。相反,孟子不仅反对好为人师,甚至“反对教学”[7]。
按照《大学》的“八条目”,学习的关键在于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的重点在于“学”,而“诚意正心”的重点在于“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点在于“行”。朱熹注《大学》,重视“格物致知”的顺序,强调“致知在格物”,视之为“明德之要”,认为《大学》古本对“知之至”缺少解释,并亲自为“格物致知”提供“补传”。[8]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强调先格物,后致知,先学(格物),后思(致知、诚意、正心)。
但是,从陆王心学的视角来看,《大学》所列“八条目”的重点在于“致知”而不是“格物”。先有“心之官则思”的致知,经由怀疑而实现了“先立乎其大者”的主见,眼前所格之物才会显露真相。相反,如果头脑空空,全无主见,眼前之物就会一片漆黑。之所以“夜间观牛,其色皆黑”,正因为观牛者缺乏光亮。致知及其主见,就是格物的光亮。之所以“致知”优先于“格物”,乃因为人有先验的“心意”(诚意正心)。只要维护了这种先验的“心意”,就可以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关系扭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合理顺序是先“正心诚意”并落实为“致知”,然后再去“格物”。王阳明将这个扭转之后的新秩序概括为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9]这四句话隐含了“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正是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旧秩序的颠倒。在王阳明看来,做到了“诚意正心致知”,就做到了“先立乎其大者”。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致知”。“诚意正心”虽然重要,但“诚意正心”必须落实到“致知”,才保卫和成全人的主体性。就此而言,“致知”比“诚意正心”更重要,也因此,王阳明将“致知”的过程称为“致良知”,并将“致良知”视为心学的核心精神(接近西方哲学所关注的主体主义)。有了“致知”(致良知),“格物”才会豁然贯通。相反,如果没有保卫和发挥人的先验的“诚意正心”及其“致知”(致良知),缺少智慧之光,“格物”就会茫然无绪,并由此发生类似“亭前格竹”那样的无效努力。[10]王阳明之所以反思自己“亭前格竹”的经历,也正是为了让后来的学者明白:“亭前格竹”乃自己少不更事的闹剧。如果一个人脑子空空、没有主见,就会做类似“亭前格竹”的蠢事。
总之,所谓启发教学,其实是愤悱学习,其核心精神不仅在于先学后教,更在于学生自学、自悟、自得之独立思考。启发教学所隐含的理论课题是学思关系。传统的教学制度主张多读书、多记忆,而启发教学主张学思结合,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陈白沙的说法是:“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11]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孟子之后,儒家正统失传两千余年。两千年之后,孟学才在周子(周敦颐)、程子(二程)、陈白沙等人那里得到延续并由此发展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的核心精神,依然是孟子所倡导的“自得”。[12]所谓“自得”,就是独立思考与怀疑,就是孟子倡导并为陆王心学重点发挥的“先立乎其大者”及其隐含的主体主义精神。
二、时习教学与知行关系
时习教学源自《论语·学而》中的一段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有三处直接讨论“习”:一是《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二是《论语·学而》将“传不习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三省”之一。此处的“习”与“学而时习之”的内涵几乎相同,但“传不习乎”之“习”更明显倾向于“践习”、“练习”或“行动”。后来,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将自己的对话集称为“《传习录》”。三是《论语·阳货》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此处的“习”明显接近现代汉语所讨论的“践习”或“练习”。
一般将“学而时习之”之“习”解释为复习。古人读书,惯于“诵读”,所以古人的复习也称“诵习”。[13]朱熹将“学而时习之”之“习”解释为“鸟数飞”,依然采用“复习、练习”的解释。[14]
有人认为,朱熹将“习”解释为复习,这是误解。因为学习并且经常复习,就不可能令人喜悦。[15]不过,复习是否一定不能带来喜悦,也难说。比如,求知者如果在复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知识,“温故而知新”,就可能收获知识创新的快乐。
但是,如果将“习”理解为“践习”或“习行”,那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学习知识并将所学的知识付诸行动,用知识来解决问题,这样的学习确实会给求知者带来更大的成就感。
因此,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学而时习之”之“习”乃“练习”或“践习”以及与之相关的习性、习惯而非“复习”。比如,杨伯峻对“学而时习之”的解释是:“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16]
其实,朱熹引述程子的观点来解释“学而时习之”时,已有提示:“学而时习之”中的“习”有践习、行动的含义。按照程子的解释,所谓“学而时习之”,就是“学者,将以行之也”。在程子那里,“习”的含义也是行动、践习、习行或习惯而不是复习。
“学而时习之”不仅提出了学与习的关系,而且强调“时习”。何晏等人将“时习”之“时”解释为“三时”:一是“身中时”,强调年龄,在适当的年龄安排适宜的诵习;二是“年中时”,强调季节,在适当的季节安排适宜的诵习;三是“日中时”,强调“一日之计”,每天安排好作息的节奏。[17]这些解释也说得通,但漏掉了“时机”这个重要的信息。
从“时机”的视角来看,所谓“时习”,就是在恰当的时间或恰当的时机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将所学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习性和习惯。时机之“时”正是孔子所看重的智慧。《论语》多次讨论“时”的智慧。《论语》不仅以“时习”开篇,而且以“天命”收尾。《论语·尧曰》最后一章提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里的“命”即“天命”,亦是“时”的智慧。《论语·宪问》有“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的说法,《论语·乡党》更重视“时”的智慧。有人认为,《乡党》一篇“皆为时中”。[18]有人甚至认为,孔学的核心并非“仁学”而是“时学”。《论语》开篇就提出“时”的智慧,或有特别的考虑。[19]孟子对孔子最高的赞叹是:“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后来程颐也强调“时”的智慧:“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20]也许,这也是孔子看重《易经》的原因:“易道深,一言以蔽之,曰时中。”[21]
与启发教学一样,时习教学也隐含了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的重大转变。从学生之学的视角来看,时习教学乃是行动学习或笃行学习,接近现代教学论所讨论的“做中学”或问题解决学习、研究性学习、项目化学习。
时习教学之所以重要,乃因为“时习”学习隐含了知行关系以及相关争议。惟立足于知行关系的视角,才可能完整理解时习教学所倡导的新方向。相反,如果不将知行关系与时习教学关联起来,就很难理解时习教学的改革目标。
虽然《尚书·说命》早就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但究竟知难还是行难,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有人认为知易行难,但也有人认为知难行易。[22]除此之外,更多学者关注知与行或理论与实践的“先后”关系。
孔子比较看重“行”。除了“习”,《论语》也多次讨论与之相关的“行”。《论语》所讨论的“行”,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知行关系之“行”。比如《论语·学而》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行”优先于“知”的知行关系。二是思行关系之“行”。比如《论语·公冶长》提出:“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每件事考虑多次才行动,孔子听到了,说:“不要思考太多,思考两次,就可以行动了。”三是言行关系之“行”。比如《论语·里仁》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的说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与之相关,《论语》也讨论“躬”,《论语·里仁》的说法是:“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如果将“习”理解为生活习惯、政治管理习惯与经济管理习惯以及相关的实践经验,那么几乎整部《论语》都在讨论“习行”,“躬行”以及“时习教学”。
在孔子那里,学思关系固然重要,知行关系却高于和优先于学思关系。学思关系的重点在于思,学贵在疑,“学而不思则罔”。即便如此,也不能疑而不决、谋而不断,不能耽于思考而不付诸行动。从“知情意”的视角来看,仅仅只有知和情而没有行动,就是缺乏意志。行动乃意志的显现。
孟子延续孔子的思路,但强化了“心之官则思”和行动精神。《孟子·尽心上》的说法是:“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比较警惕“死读书”而倡导怀疑、思考和批判性阅读。《孟子·尽心下》的说法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宋代陆九渊更重视生活实践并在实践中发明本心。他提出的“就日用处开端”接近禅宗哲学推崇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或“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顿悟”学说[23],也提前预演了明代湛甘泉倡导的“随处体认天理”[24]。
朱熹认为陆九渊虽然“气象甚好”,却有“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陆九渊集·答张南轩》卷三一)的问题。朱熹的批评也可以反证陆九渊对“行动”和“践履”的看重。正因为看重实践,较少书呆子气,所以看起来“气象甚好”。朱熹虽然明确提出“知行常相须”,却也判定“知轻而行重”(《朱子语类》卷九)。
陆九渊的思路在王阳明那里获得更丰富的解释和扩充。在“就日用处开端”和“知行常相须”的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王阳明全集·与道通书》)。王阳明的“老师”陈白沙(有学者认为陈白沙是王阳明学说的真正教父[25])更重视行动,甚至认为读书太琐碎,必导致愚笨。他虽然较少著述,但自认为超过著作等身的大儒郑玄。他宁愿劳动、爬山、唱歌,也不屑于埋头“著书”(《白沙先生行状》)。《咏江门墟》则直接提出“耕读传家”和“半农半儒”的主题:“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
启发教学所重视的学思结合与时习教学所重视的知行合一,两者一起构成《中庸》所倡导的五步教学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按照湛甘泉[26]和王夫之[27]等人的解释,“学、问、思、辨、行”五个步骤可进一步压缩为三个关键步骤:一是学问,即博学(阅读和见闻)、审问;二是思辨,包括慎思、明辨;三是笃行,不仅练习或操练,而且将知识运用于解决实践问题。这样看来,可以将“学、问、思、辨、行”简称“学思行”。“学”即学与问,不仅阅读,而且提问,提问包括提出好的欣赏与不好的质疑;“思”即思与辨,提出欣赏和质疑的主见之后,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决自己的提问或与他人讨论、辩论;“行”即笃行,日常的笃行包括复述、练习与自我反思。[28]
总之,所谓时习教学,其核心精神是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生活实践。时习教学所隐含的理论课题是知行关系。从知行关系的视角来看,时习教学接近现代教学论所讨论的“做中学”或“教学做合一”、问题解决学习、研究性学习或项目化学习,也触及了现代教学论所讨论的“教育即生活”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惟立足于知行关系的视角,才可能完整理解时习教学的真义。相反,如果不将知行关系与时习教学关联起来,就很难理解时习教学所引领的改革意图。
三、兴发教学与情理关系
启发教学与时习教学一起构成了《中庸》所倡导的“学思行”。启发教学与时习教学及其“学思行”虽然有重要的教学改革意义,但两者的重点都在于改变学生的学而较少关注教师的教。启发教学的重点是愤悱学习(接近现代教学改革中的发现学习或自学辅导),时习教学的重点是行动学习(接近现代教学改革中的做中学、研究性学习或项目化学习)。两者对教师的教皆缺乏具体的解释。缺乏教师的教的后果是,如果学生不愿意学习、缺乏学习的动力,学习就不会发生。这正是兴发教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兴发教学并非不相信学生具有主动学习的先验主体性,但兴发教学坚持:人虽然有主动学习的先验主体性,但人的主体性及其主动学习容易被他人或环境压抑、压制,人的先验主体性一旦被压抑、被“流放”,教育者就需要通过兴发教学的方式使学习者“求其放心”。
兴发教学源自《论语·泰伯》中的一段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谓“兴于《诗》”,其实是“兴于《诗经》”。在孔子看来,《诗经》的主要功能有三:一是调节情感。《论语·八佾》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二是净化情感。《论语·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是入学门径。《论语·阳货》提出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类似的说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也因此,孔子特别看重“诗教”。《论语·阳货》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孔子那里,《诗经》尤其是“二南”乃求学之门径。不学“二南”,犹如“正墙而立”,一物无所见,寸步难行。《论语·季氏》的说法是:“不学诗,无以言。”孔子两次感叹“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有人由此认为,诗教及其所看重的“兴发”正是中国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精神。[29]孔子之所以重视“诗教”,也正因为“诗,可以兴”的兴发效应。
之所以“诗,可以兴”,因为诗与诗教主要关涉人的情感,其背后隐含了教学理论研究领域所关注的“情理关系”。在情理之间,西方教育哲学不乏重视“情感”的哲人,比如英国哲人休谟(Hume)认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30]但是,相对而言,中国教育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更看重“情理关系”中的情感因素。
诗教重视人的情感,但并非停留于情感。诗教的真正目的在于“以诗言志”。《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庄子·天下》《荀子·儒效》《礼记·孔子闲居》《史记·乐书》《说文解字》皆有类似的说法。“诗言情”与“诗言志”原本一体,相互发明。
立足于“诗言志”之诗教,主要通过情感的兴发发展人的主体性。这也正是陆王心学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关键差异。程朱理学更看重“理性”而警惕人的情感欲望;陆王心学更珍惜人的情感欲望,尤其重视人的主体性。如果说程朱理学推崇礼教而倾向于理性主义教育哲学并由此压制人的主体性,那么陆王心学则推崇诗教,倾向于情感主义哲学,并由此尊重并高扬人的主体性。 在程朱理学那里,为学的关键在于“读书”,而陆王心学却强调在读书之前,要“先立乎其大者”。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不仅指向“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做人,而且鼓励学习者发挥并稳固建立人的主体性。陆九渊强调,即便不识字,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人(《陆九渊集·语录上》卷三十四)。陆九渊并不反对读书,他只是强调学者要“先立乎其大者”,然后才可以读书。只有保卫了人的先验主体性,才可能激发出基本的自信心与掌控感。陆九渊强调的“大者”,几乎就是孟子的“大丈夫”气象。后来,王阳明将孟子和陆九渊重视的“先立乎其大者”进一步扩展为“致良知”(《王阳明集·续编一·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卷二十六)。无论“先立乎其大者”还是“致良知”,其核心皆为人的主体性。
陆王心学的源头是孟学。心学教育哲学普遍尊孟,都以孟学为儒学正宗。孟子尤其看重人的情感,即便他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31],但“寡欲”也并非“无欲”或“禁欲”。孟子之寡欲并非以理性压制人的情感,尤其反对以理杀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32]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反复论证孟子并不排斥人的正常情感欲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33]即便王阳明谈论“存天理,灭人欲”,他对天理的理解也不同于程朱理学的解释。在程朱理学那里,天理就是外在的道德伦理与自然法则,而在王阳明这里,天理就是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及其主体性。也因此,王阳明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发明人的内在本性、良知及其主体性。良知和主体性是人的本能,遗憾的是,后天环境容易使人的先验良知及其主体性被压抑、被“流放”。只要“求其放心”,回归人的本性,把人的先验主体性还给学生,就可以实现“自求自得”的教育目标。
孟子教育哲学以及陆王心学的贡献在于,人性中的自然本能和先验良知被承认、被肯定。这样的观念有助于个人发挥其主体主义之自我修行精神。过度强调“灭人欲”和“性恶论”,可能会导致压制或消减人的主体性。相反,珍惜人的情感欲望,承认“人性善”,可能会带来人性的解放和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尊重。
孟子尊奉孔子的教育哲学,但两者亦有细节上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孟子》开篇就讨论“义利之辨”。仁义貌似邻近,实则不同,甚至彼此对立。《周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样看来,仁义的差别类似柔刚的差异。仁乃慈善之爱,偏重情感,仁即仁爱;义乃刚毅之勇,偏重理性,义即侠义。董仲舒的说法是:“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或曰,义是“严于律己”,仁是“宽以待人”。可见,仁义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情理关系或情义关系。《孟子》之“义”,既指“情义”,也指义气、侠义、义务。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重视《诗》《书》,但孟子特别重视《春秋》。孔子虽作《春秋》,但《论语》却对《春秋》只字不提。孟子之所以重视《春秋》,也正因为《春秋》蕴含了令“乱臣贼子惧”的“义”观念。所谓“春秋无义战”“春秋大义”或《庄子·天下》所言说“《春秋》以道名分”,皆与《孟子》重视的“义利之辨”有内在关联。除了指义气、侠义、义务之外,《孟子》之“义”直接指向“义政”。[34]仁政可能走向家长制的专制,而由仁政发展出来的义政可能走向民主制。这就是《孟子·尽心下》提出的“民贵君轻”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认为,孟子将《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所讨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发展到了一个高潮。[35]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隐含了他所推崇的主体性及其民主观念。
孟子教育哲学的精华就是宣示人的先验良知及其主体性。孟子本人的个性也是铮铮傲骨与一腔正气,宋儒的说法是:“孟子有些英气。”[36]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或曰:“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此类“大丈夫”形象,显示孟子哲学的主体主义或唯意志主义。也因此有人认为:“《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气节的培养上,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37]康有为因孟子传《春秋》而尊孟,认为孟子“乃孔门之龙树、保罗”。荀子传《礼》,而孟子传《诗》《书》《春秋》。荀子传小康世、据乱世之道,而孟子传大同、太平世之道。[38]又谓,孟子为《公羊》正传,荀子为《榖梁》太祖。[39]梁启超也一度以“絀荀申孟”为己任,发动“排荀运动”。[40]
孟子不仅宣示人的先验良知及其主体性,而且开发了“致良知”及其“主体性”的具体路径。孟子自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自求自得,勿忘而且勿助,不“好为人师”,不“揠苗助长”。“揠苗助长”是中国儒家教育学的经典案例,堪称中国儒家教育学推崇“自然法”的经典范例。“养气”的关键在于“勿忘,勿助长”。“不耘苗”是“忘”,“揠苗”则是“助长”。不揠苗助长的前提是勿忘勿助,不“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特别提醒:“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之所“患”,重点在“好”。“好为人师”者必疏远“勿忘勿助”的原则甚至“揠苗助长”。另外,好为人师者,必自满自负,不思长进。“若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此人之大患也。”[41]二是坚持正义,以道、义养护人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说法是:“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浩然之气乃由平时“集义”所生。按朱熹的解释,“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42]。儒道两家都重视“养气”,但养气的方式不同。道家的“养气”是“爱精”,而孟子的“养气”是“集义”。有人认为,就人格气象而言,“孟子略同于庄子,荀子则近似老子。因此在某些方面,庄老之异或孟荀之异反而大于儒道之异。”[43]三是坚持意志主义,坚守大丈夫形象。《孟子·滕文公下》将其归纳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相关的说法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之豪迈,大概只有庄子可与之比肩。
兴发教学及其所隐含的情理关系之所以重要,也正因为兴发教学珍视人的情感欲望以及人的生命本能。在种种情感欲望之中,人们往往关注“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隐含的求生欲望,却容易忽视人对尊严与自由的渴望。尊严与自由的背后是人的主体性。就此而言,所谓兴发教学重视人的情感欲望,其实就是重视人的主体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尊严与自由。
从兴发教学的视角来看,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人的主体性。为了发展人的主体性,教育者至少需要做到三个“还给”:一是把参与决策的权利还给孩子,让他自信;二是把尝试错误的权利还给孩子,让他自学;三是把有所热爱的权利还给孩子,让他自得其乐并自食其力。
总之,兴发教学的核心精神就是重视人的情感及其主体性。就此而言,兴发教学几乎就是尊重教育与自由教育。尊重与自由既是兴发教学的目标,也是兴发教学的途径。如果教育者满足了儿童求尊重与求自由的需要,就实现了兴发教学的目标。如果教育者想了解兴发教学的途径与方法,那么,最佳的途径和方法就是对儿童表达尊重并给他自由。也正是在这点上,兴发教学与启发教学、时习教学存在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兴发教学就是兴起和引发人的情感或激情。实际上,兴发教学的关键在于兴起和引发人的主体性。对学生而言,发展主体性的具体途径是“学思结合”和“知行结合”。对教师而言,发展学生主体性的具体途径是“兴发教学”。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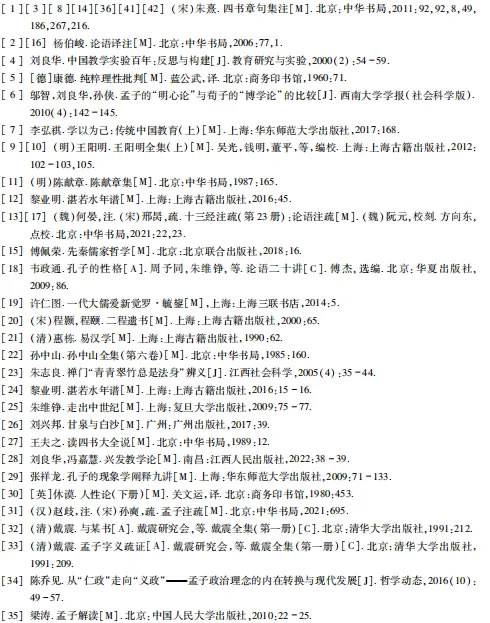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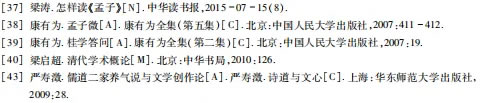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