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 殷玉新 王丽华 已有0人评论 2020/5/18 14:33:38 加入收藏
导读:知识选择是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基本问题,教材知识选择作为教材建设的基本问题,不仅涉及学校教育应该选择什么知识供学生学习,更涉及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如何选择值得学生学习的知识。从社会变革和课程与教学变革对教材知识选择提出的要求来看,从“选什么”到“如何选”是教材知识选择理论基础的发展趋势。据此,本文建议教材知识选择要立足于教材知识选择的育人价值,建立“选什么”和“如何选”的综合机制,也不能忽视教材知识选择的价值导向。
一、问题提出
教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还承载着知识背后的社会规范或价值,蕴含着认识世界的特殊模式。[1]而且在我国,教材作为课程实施的关键载体,在落实立德树人和国家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教材建设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厚的实践经验,然而在教材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则相对薄弱。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零星的教材研究多是批判性、质疑性的,对已开发出来的、正在使用的教材进行批判性、挑剔性的审视,发现其存在的各种缺陷,而关于教材原理性的思考和研究极为少见。[3]为了解决教材研究成果薄弱等问题,国家专门成立了教材局,并于2018年年底建立了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除了为国家教材建设提供咨询、编写指导等专业服务,研究基地的关键职责还在于梳理教材建设的已有经验、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围绕基础理论、实践应用和国际比较等方面,进行系统的专门研究,旨在为我国教材建设提供科学的、扎实有效的理论基础。这表明我国对教材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逐渐被提上了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日程。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教育(包括教育研究)应该更多关注知识,包括知识的创造、获取、认证以及知识的使用方式,因为如何使用知识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4]其中,知识选择是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因而教材知识选择也是教育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研究的关键内容。那么,知识选择在教材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有研究者从知识变革的视角,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教材建设过程进行了审视,发现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知识不确定性情境下教材内容更新的“相对滞后”;知识规范性检视下教材结构的“理法不足”;知识特色性关照下教材建设的“个性欠缺”等。[5]此外,教材管理的相对开放,导致部分教材质量不高、把关不严,甚至出现严重的知识性和政治性错误。[6]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教材建设在知识选择依据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教材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教材建设根本不能忽视其在社会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知识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不确定的、知识爆炸的时代,如何选择合适的知识成为教材建设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关键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
此外,从教材研究的国际视野来看,教材研究出现了历史视角、社会或文化视角、方法视角和课程视角等多重理论视角[7],但是具体来看,不同视角下的教材研究对于知识选择基础的探讨依然很薄弱。因此,找到适切的教材知识选择的理论基础或知识基础(intellectual bases)是开展科学的教材知识选择和教材建设的关键。换言之,只有厘清教材建设过程中知识选择基础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趋势,才能建设更高质量的教材,才能更好地发挥教材作为知识载体的价值,促进学生学习以适应快速的社会变革和发展。
二、教材知识选择“选什么”的理论基础及反思
在课程发展历史过程中,关于课程与教学知识选择(curriculum selection)问题的讨论始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59年提出的经典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传统的学校教育面临着巨大冲击,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学校教育只有教授像拉丁文、希腊文等古典人文知识,才能将学生培养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而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科学知识却被拒之门外。换言之,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迫使人们对知识的价值进行反思。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斯宾塞在抨击传统古典教育知识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知识价值论的思想,对教育改革和课程知识选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批判了人们对知识装饰价值的过分重视,即当时学校教育,乃至整个社会考虑的都不是什么知识最有真正的价值,而是什么知识能够获得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敬,做什么最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怎样表现才最神气。[8]在此情况下,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到的知识很少能够在社会中使用,这种知识鲜有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据此,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经典之问,关注在学校教育中应该“选什么”知识供学生学习,奠定了一百多年来教材知识选择的理论基础——选择什么知识才最有价值。
那么,在斯宾塞看来,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教材应该“选什么”知识才是最有价值的呢?他认为首先要制定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以弄清楚各项知识的比较价值,而这个尺度是能够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的尽职程度。也就是说,按照能够为完满生活做准备的贡献,对已有知识进行比较,衡量或判断各类知识的实用价值。接着,斯宾塞按照对人们完满生活做准备的重要程度,将主要知识的实用价值进行了比较和排序,分别是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准备做父母的知识、准备做公民的知识和准备生活中各项文化活动的知识五大类别。同时,斯宾塞认为不同知识的价值也有所不同,有的知识(如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内在价值,有的知识(如语言知识)具有半内在价值,有的知识(如历史知识)具有习俗价值。最后,斯宾塞得出结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因为科学知识在为人们完满的生活做准备时的价值最大。科学知识可以帮助人们直接保全自己或维护生命和健康,为了谋生间接地保全自己,为了正当地履行父母的职责,每个公民合理地调节其行为,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以及为了智慧、道德和宗教训练的目的,只有科学知识最有价值。
斯宾塞也认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教材知识选择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因为在制定一个合理的课程之前,我们需要确定(未来的)学生最需要知道什么,弄清楚各项知识的比较价值。[9]那么,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教材知识选择的本质要义在于学校教育应该选择什么有价值的知识(科学知识)供学生学习。总体来说,“斯宾塞之问”是对教材知识选择“选什么”的回答,奠定了教材知识选择应该“选什么”的理论基础,对选择什么样的科学知识作为教材内容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第一,受客观中立的知识观支配。在斯宾塞时代,受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模式的影响,知识普遍被认为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具有客观规律性,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毫无关系。就斯宾塞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科学来说,其价值不是仅凭舆论就可得来的,而是同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一样固定不变的,其真理既是必然的,又是永恒的。[10]换言之,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的理论基点在于知识的客观价值,即关注知识本身是否有利于为完满的人生做准备。据此论断,教材知识选择应当选择为完满的人生做准备的、科学的客观知识,即斯宾塞主张选择已有的、科学的、客观的知识作为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的对象。问题在于如果教材只选择客观知识,不仅会忽视知识的主观价值属性,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会使人们忽视如何选择知识的问题,遮掩了知识选择的过程。
第二,知识选择的“被动性”。为了改变以往学校教育重视知识装饰价值的弊端,斯宾塞主张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为此,他比较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已有知识的价值,最终选择了科学作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人类只能“被动”地选择知识,因为所选的知识只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科学的、客观的知识。例如,要素主义者选择了永恒学科和永恒知识;进步主义者选择了“活动”和“经验”;结构主义者选择了学科的基本结构;现代课程理论之父——泰勒(Ralph Tyler)选择了有利于达到教育目标的学习经验。无论是永恒学科和永恒知识、“活动”和“经验”,还是学科的基本结构、有利于达到教育目标的学习经验,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已有的存在。因此,在斯宾塞论断的影响下,教材编写者“被动”地选择人类社会生活存在的科学知识作为教材内容,以实现知识的功利主义价值——为完满的人生做准备。实际上,选择客观存在的知识也体现了这种“被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素养。
第三,普适划一的知识选择范式。斯宾塞将科学视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在高度推崇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课程开发”为典型特征的课程行动范式。在此基础上,课程研究关注的是将课程视为“学校材料”的“制度课程”,追求的是“价值中立”的课程开发理性化程序,从而导致“程序主义”的课程研究倾向[11],即课程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遵循理性化程序的“技术”开发问题,如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提出的“活动分析法”(activity analysis)和查特斯(Werrett Wallace Charters)提出的“工作分析法”(job analysis),尤其是集大成的“泰勒模式”。据此,指向“选什么”的教材知识选择行动范式是遵循科学、理性化的程序进行教材开发,强调的是通过合乎规律的行为对环境加以控制的人类基本兴趣,实现一种普适性的、划一性的教材开发模式。[12]在此过程中,教材选择的知识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知识。实质上,“课程开发”范式下的教材知识选择指向的是选择什么知识。然而,这种以“最有价值的知识”为目标的、普适划一的教材开发模式难以适应当前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价值冲突的课程与教学情境,如果现实中的教材开发仅采用这种普适划一的模式,必然导致课程与学生学习陷入困境。
在课程与教学的知识基础演进过程中,诸多学者对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美国批判主义教育学者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 Apple),他认为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并没有错,但批判这个问题“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化”色彩,因为学校教授什么知识不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更涉及政治领域或意识形态的问题,即教育和课程(包括知识选择)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种族、性别等政治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据此,阿普尔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Whose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的问题,为衡量课程与教学领域的知识价值提供了“人的尺度”[13],也为教材知识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是,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对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进行的诸多批判,依然没有超越学校教育应当“选什么”知识供学生学习的范畴,无论是阿普尔主张重视“谁的知识”,还是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强调的“强有力的知识”(powerful knowledge),其实质依然属于“选什么”知识的范畴。换言之,一百多年来我们进行教材知识选择的理论基础依然没有超越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
三、教材知识选择面临“如何选”困境的由来及可能性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爆炸时代,知识的总体容量在不断膨胀,知识的更新速度也在飞速增长,如何选择合适的知识供学生学习成为当代教材知识选择的难题。这一难题似乎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因为当前学校教育所教的很多知识都没有学习价值,而且忽略了那些具有学习价值的知识,导致人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所需的知识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如何为学校教育选择“值得学习的知识”成为当前人们密切关注的时代话题。[14]在重新面对斯宾塞所批判的“忽视了社会生活中能够实际应用的知识”的现实困境,人们对学习者到底该学习什么知识有了新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如何选择有价值的知识成为学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例如,近些年很多研究主张基于核心素养或学科素养选择有价值的知识作为学习内容,在建构“21世纪必备能力”“21世纪核心素养”等值得学习的知识清单基础上,挑选教材知识选择的对象。据此,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于2014年从“生活价值”的视角提出了“什么知识值得学习?”(What's worthy learning?)的时代之问,立足知识的“生活价值”选择值得未来学生学习的知识。实际上,珀金斯“什么知识值得学习”的论断可以作为当前教材知识选择的理论基础,因为其为教材知识选择“如何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那么,在珀金斯看来,如何为学生选择值得学习的知识,尤其是在复杂的未来社会?珀金斯的判断非常直接,他通过论述传统学习过分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掌握了解性知识、强求专业知识,发现传统学习总是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陷入被动。珀金斯认为之所以传统学习会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陷入被动,是因为传统学习忽视了知识的真实内涵以及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在此基础上,珀金斯认为在对教育进行构想时,基本出发点在于尝试设想我们所教授的知识内容中哪些对学生的生活有价值[15],即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才值得学习。也就是说,知识只有能在某种生活情境中得到实际运用,才值得学习。为了使值得学习的知识在生活中能够得到融会贯通,珀金斯对真正的知识学习进行了论述,即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学习旨在“为生活做准备”(life-ready)。据此,他认为真正的学习需要真正地理解知识,只有真正地理解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思考,因为只有学生具有思考能力和有效的思维,知识的学习才能真正地为生活做准备。同时,将知识的理解和思考转化为广泛的应用和一系列的意义建构。最后,珀金斯指出教育的本来目标在于促进具有生活价值的学习,在此过程中教授学生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实现智慧的通达,是一种未来的智慧。因此,珀金斯建议从“未来智慧”的视角看待教育,实现为未知而教(educating for the unknown),学生才能够参与为未来而学的实践。
在21世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逐渐发现了停留在“熟悉、了解”水平的百科全书式教育的弊端。珀金斯就曾指出,堆砌在教科书里的大量信息,本身定位就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学习者即将面对的世界是灵活多变的,兼具未知与已知。[16]那么,在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价值冲突的时代环境中,“什么知识值得学习”的论断对如何选择教材知识有何影响呢?
第一,指向为了理解的教与学的理论基点。珀金斯一直强调为了理解的教与学(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understanding),因其能够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科学和正确的理解,促进学生整合知识、应用知识等能力的有效提升。[17]在《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一书中,珀金斯再次强调,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学习,需要并理解影响力较高的知识,它们应在实际生活中被直接运用,并能够支持实践、政治、社会及审美等各方面多样化的终身学习。[18]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为了理解的教与学,学生才能够对知识进行综合理解并在生活中应用,知识才真正具有生活价值。那么,在“什么知识值得学习”背景下,教材知识选择的理论基点就在于实现为了理解的教与学,即实现为了理解的教与学应当成为教材知识选择的指导思想。
第二,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知识选择观。珀金斯强调知识的主动选择,不仅要主动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也要创造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在知识更新速度飞快的今天,很多传统知识依然具有生活价值,应对这些知识进行主动选择,而不是抛弃。在珀金斯看来,教材不能以原有的方式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传统经典知识,而应以“宏观保留”(big save)的方式重构经典知识。[19]在此过程中,人们也不能盲目地将所有的传统经典知识纳入教材,应以重构的方式改变学习内容和学习视角。比如,减少函数的理论性知识和内容,增加对函数实践性知识的关注,将使用函数看待世界的方式纳入教材之中。此外,面对繁杂的知识世界,珀金斯以“宏观选择”(big choices)的方式较为隐晦地提出了对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的创造。在进行“宏观选择”时,珀金斯建议我们可以怀抱着勇气和怀疑的态度,哪怕是怀疑我们自己熟悉的、对于“教什么”的直觉。[20]也就是说,只有将创造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的行动付诸实践,教材所承载的知识才可能真正具有并发挥生活价值。因此,在进行教材知识选择的过程中,不仅要主动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也要创造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
第三,追求综合灵活的知识选择范式。虽然阿普尔在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时,将课程研究由“课程开发”转向“课程理解”,但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内在统一的。课程开发过程包含着对课程意义的某种理解并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为课程与课程事件赋予新的意义,而要真正使这种意义实现出来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找到“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的结合点。[21]而珀金斯提出的“什么知识值得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课程开发”和“课程理解”。因此,按照珀金斯时代之问的观点,教材知识选择的行动范式既重视“教材开发”的实践,开发具有生活价值的教材,又强调“教材理解”,理解教材背后实践、政治、社会及审美等承载的内在价值。
在课程与教学知识基础的演进过程中,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为很多课程与教学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理论或知识基础。但是,面对21世纪知识爆炸时代,以及知识情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课程与教学知识选择的影响逐渐式微,因为当前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选择值得未来学习的知识。[22]因此,根据珀金斯的观点,尤其是从课程与教学变革对教材知识选择的要求来看,从“选什么”到“如何选”是未来教材知识选择的趋势。
四、对我国教材知识选择的启示
袁振国教授认为面向未来的教材研究,特别要关注教材内容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教材编写与现实生活中知识应用的关系、教材呈现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以及多个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的要求。[23]因此,在立德树人和核心素养的时代背景下,教材知识选择知识基础的研究可以为面向未来的教材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实质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知识选择观蕴含着不同的知识旨趣:斯宾塞的经典之问关心的是当时的学校教育应该“选什么”知识供学生学习,而珀金斯的时代之问聚焦的则是当前教材应该“如何选”有价值的知识供学生学习。那么,在教材建设过程中,该如何看待或审视从“选什么”到“如何选”的教材知识选择观的发展趋势呢?
(一)立足教材知识选择的育人价值
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对新时期“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做出了明确规定,首次提出“核心素养”概念,在此背景下,教材知识选择应该将育人价值作为其终极目标。从教材观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其呈现出从相对封闭向相对开放、注重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以及整合性的方向发展,教材不仅被看成是传承人类文化知识的载体,更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的、体现人文关怀的意义开放系统。[24]因此,教材知识选择应该关注学生学习,发挥其育人价值。就教材开发而言,无论是“一次开发”时学科专家对教科书的设计、编订和制作,“二次开发”时教师依据其教育理念、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对教材进行重新理解、组织、加工和输出,还是“三次开发”时学生依据其兴趣、经验、知识基础和对时代、社会的感受,对教材的知识、信息和教师的解释所进行的接受、理解、调整、改造乃至批判,[25]都要立足于教材的育人价值。换言之,教材知识选择的每个环节都要立足于教材的育人价值,从而帮助学生获得具有生活价值的科学知识,应对未来的生活。
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指向的是知识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知识的育人价值。从其承载的教材知识选择观来看,每个学科都有独特价值,学科专家应根据学科发展特点选择有价值的知识和人类经验作为教材内容,无论是知识的组织与整合,还是内容编排方式等方面,都要符合知识的学习特点和基本规律。而珀金斯提出的“什么知识值得学习”更加强调的是知识学习后的运用价值。根据珀金斯的观点,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知识才值得学习,那么,教材知识选择就要结合学生获得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情况,及时更新教材内容,确保其具有生活价值。此外,学生在知识应用过程中表现出的态度、心理性向都体现着教材知识的育人价值。而且阿普尔在批判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的基础上,建议我们要关注在知识—权力结构中学生身心的成长境遇,也反映了对教材知识选择育人价值的重视。因此,教材知识选择要在保持教材建设基本方向的前提下,立足于其育人价值,既强调学生是知识学习的主体,关注学习者的心理发展规律,建设符合学生心理发展逻辑的教材,又要发挥学生在教材知识选择上的作用,如鼓励学生依据其兴趣、经验、知识基础和对时代、社会的感受,对教材进行接受、理解、调整、改造乃至批判,实现对教材的“三次开发”。
(二)建立“选什么”和“如何选”的综合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除了面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巨大挑战之外,知识的更新速度前所未有,时代发展也带来了不确定性,新时代背景下的教材建设要以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知识基础为支撑。从支持教材知识选择的理论基础的演进历程来看,在面对不同的知识选择问题时,“斯宾塞之问”关心的是“选什么”,即选择什么知识作为教材内容;“珀金斯之问”关注的是“如何选”,即如何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作为教材内容,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异的教材知识选择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珀金斯的时代之问与斯宾塞的经典之问一样,都没有普遍且唯一正确的答案,需要根据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进行与时俱进的思考。[26]问题在于我国教材内容更新“相对滞后”,以及教材结构“法理不足”,表明教材知识选择存在“选什么”的难题;教材建设的“个性欠缺”,忽视创造性,表明教材知识选择也存在“如何选”的难题。[27]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教材知识选择应当建立“选什么”和“如何选”的综合机制。
首先,就教材知识选择“选什么”的机制来说,教材知识选择既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和谐生活融入教材内容,体现时代特性,凸显不同学科知识的特有价值与学科特性,又要关注学生兴趣、身心发展的差异,发展学生个性,实现教材的育人价值。其次,就教材知识选择“如何选”的机制来说,为了应对新时代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1世纪知识和技能”与“核心素养”体现了课程与教学显著的时代性,那么,在进行教材知识选择时,不仅要关注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也要关注知识内容的时代性,摒弃陈旧的、落后的知识,与时俱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教材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如果不将教材的功能定位于学生,则凝练的学科知识就是抽象的存在,教学文本、教学指引的意义也就无从体现,官方意图、官方知识只会落空不会落实[28],教材的价值和功能也将无法真正体现。因此,教材知识选择也要考虑学生,思考将教材功能定位于学生的教材知识该如何选择。总而言之,我们要建立“选什么”和“如何选”的教材知识选择综合机制,不仅要重视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科学知识作为教材内容,也要紧跟时代需求和学生特点,还要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代相应的主流价值观对教材知识选择的影响。
(三)不能忽视教材知识选择的价值导向
受到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的影响,阿普尔提出不仅要重视知识本身的客观性,更要重视知识背后的价值导向。在当时,他就发现课程社会学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缺陷:教科书仅是一种传递意识形态内容的辅助手段,由占支配地位的隐喻、形象和关键的思想构成,而意识形态充满了各种价值观、信念和思想,可能导致错误的意识。[29]可以说,阿普尔在转变当时课程社会学研究对教材研究的误解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因此,虽然阿普尔对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进行了诸多批判,却依然没有超越学校教育应当“选什么”知识供学生学习的范畴和高度,但其对课程教学领域诸多问题的讨论依然有特殊的价值。例如,阿普尔曾论述了学校获得“合法性知识”(legitimate knowledge)的最主要途径——教科书,他认为教科书作为“合法性知识”的载体,是统治阶级选择的知识负载价值的进一步强化,规范着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内容及其体现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因此,要对教科书本身以及其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那么,我们在进行教材知识选择时不能忽视知识背后的价值导向作用。
首先,就价值导向对教材应当“选什么”知识的价值规范来看,除了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科学知识作为教材内容,也要选择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知识,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迎接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巨大挑战。其次,就价值导向对教材应当“如何选”知识的规范来看,我国教材知识选择必须以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指导,形成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体系。因此,我国新时代的教材建设还必须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不断完善教材编审制度、教材选用制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材建设,切实保障教材建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进而始终保持我国教材建设方向的正确性。[30]换言之,阿普尔提出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可以为教材知识选择提供重视价值导向的警示。
此外,教材对使用者有着潜在的、隐性的、深刻的影响,教材研究者正在努力发展教材理论,话语理论、媒体分析和知识社会学等都成为教材研究的理论基础,开展不同视角的、跨学科的教材研究。[31]因此,除了为教材建设提供实践意义,从知识基础的视角探讨教材知识选择也有利于为开展全方位的教材研究提供学术支持。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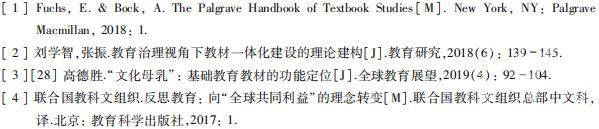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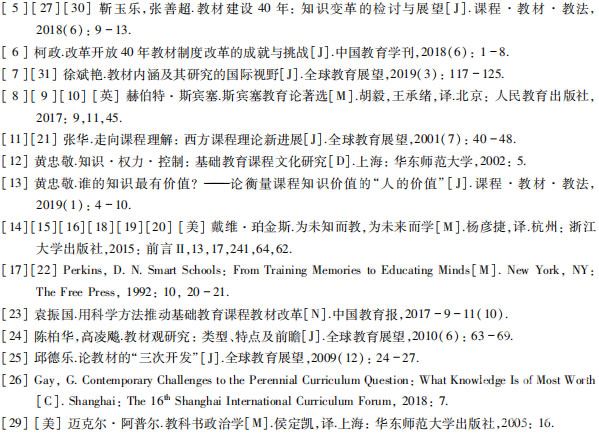
(作者:殷玉新,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王丽华/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国创新教育网 版权所有:站内信息除转载外均为中国创新教育网版权所有,转载或摘录须获得本网站许可。
地 址:潍坊市奎文区东风大街8081号 鲁ICP备19030718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
鲁公网安备 37070502000299号